撰文 | 林孜
《追寻绿色中国》一书回顾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环境保护和发展博弈,带来了什么启示?

▲江苏省宿迁市的淮河风景带。图片来源: Zhang Lianhua / Costfoto / Sipa USA / Alamy
如果把时针从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2020年倒拨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一个环境危机频发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迎来被称为“时代红利”的高速增长期。证券市场兴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深度融入全球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19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突破13%,创造了全球罕见的增长奇迹。
然而,支撑这一奇迹的是密集发展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环境问也随之加剧。沿河化工、造纸、印染等重污染企业导致淮河水质漆黑如墨,流域癌症村频现;广东贵屿成为“全球最大电子垃圾村”,重金属污染导致土壤无法耕种;2011年冬,北京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522微克/立方米,空气污染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在环境危机中,一批环保人士、学者与政府官员挺身而出,推动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红线划定、环境信息公开等制度创新,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环境的中国特色环保之路。
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在经济与环保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是如何走出污染阴霾?又是什么促使决策者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话地球采访了《追寻绿色中国》一书的作者马天杰,回顾中国三十年来绿色转型的艰难探索与关键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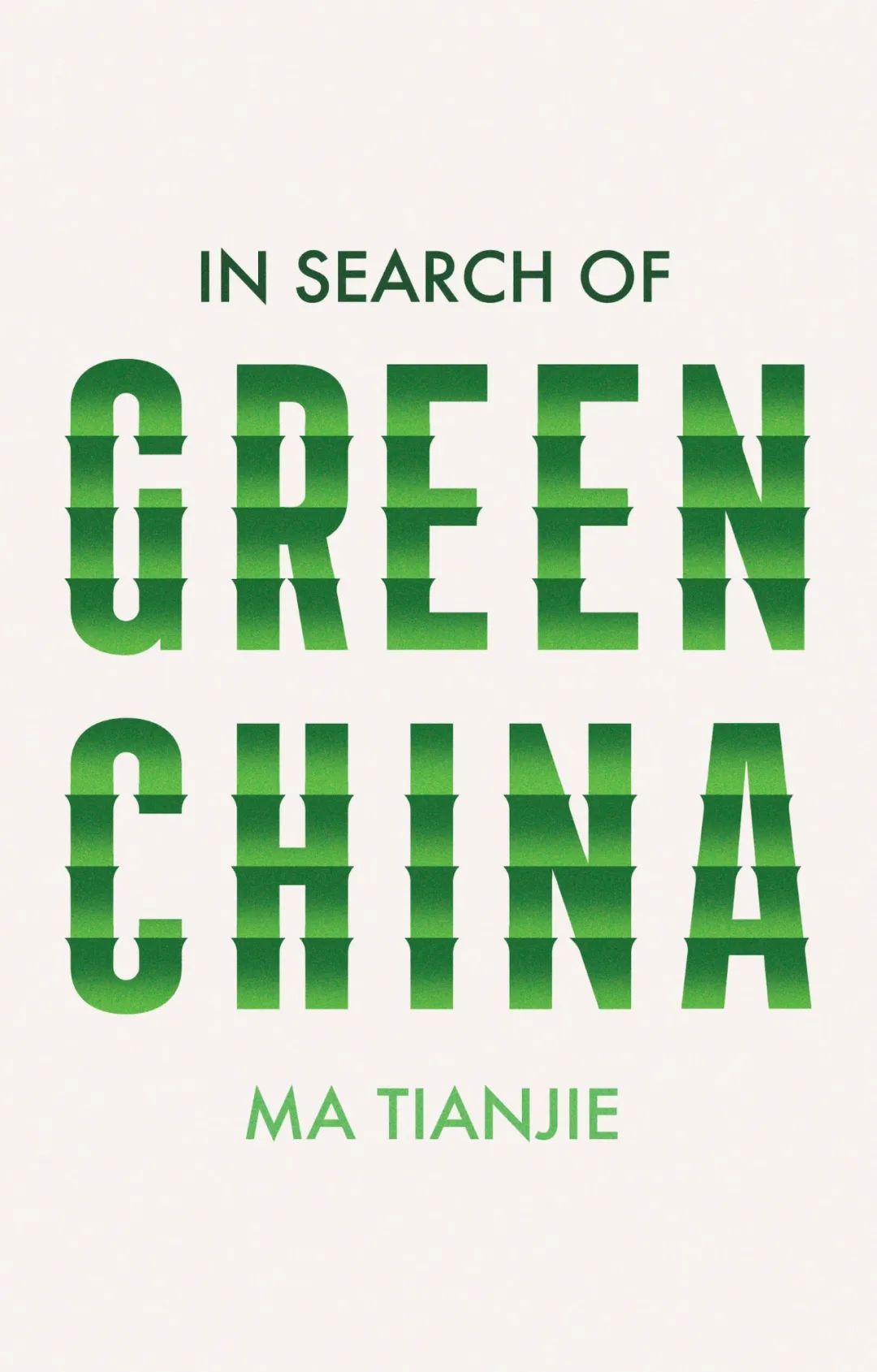
图片来源: © Polity Books
对话地球: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决定回顾和记录中国三十年来的环保历程?
马天杰:当年我在为中外对话(现对话地球)进行环境报道写作的时候,接触到了很多早期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材料,有一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上世纪90年代涌现了好几部关于淮河污染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中提到河边的一座动物园里的猴子,被河水中刺激性的污染物熏瞎了眼睛。1993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发起了第一届“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把淮河污染触目惊心的状况呈现给了全国电视观众。这也是中国公众第一次比较直观接触到环境破坏的严峻现实。这些三十年前的生动材料,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之后轰轰烈烈的环境治理行动的起点,但对今天的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已经有点陌生。然而,不了解这些往事,就很难理解近几年中国环境状况所发生的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怎么发生的?背后经历了什么样的博弈?这个过程没有太多人记录下来,这也是促使我动笔的初衷。
对话地球:书中讲述了中国几个里程碑式的环境事件,从淮河治污到雾霾治理,从反对怒江大坝到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从“环保风暴”到“双碳目标”的提出,在你看来,中国的环保运动在观念与策略上有什么演进?
马天杰:2013年治理雾霾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无论是民间环保组织,还是像潘岳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绿色思想者,都构想通过一种自下而上、多方制衡的方式,对中国当时占据主流的极端的发展主义进行一种修正。当时一切向GDP看齐, 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绑定,以短期经济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去进行关于发展的决策。而由环保NGO、环境记者、律师等等所组成的绿色的民间力量, 对于当时的发展主义倾向起到了挑战和制衡的作用。
但是到雾霾治理的时候, 这个模式发生了一个转变。2012年,生态文明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后面又被写进党章,乃至宪法。这意味着中央在理念层面基本上抛弃了极端的发展主义。这个过程可能从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已经开始。当生态文明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的时候, 就表明中国已经不再追求单纯以GDP为中心的、以总量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理念先行的环保主义走上了舞台,之前制衡极端发展主义的民间力量,他们的使命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新的模式下它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过去这十年以来, 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浙江省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的PM2.5监测仪。图片来源:Imago / Xinhua / Alamy
对话地球:你在书中提到了环境治理的“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优势和局限性?
马天杰:中国环境治理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这跟西方所走过的环境保护道路有根本的区别。西方的保护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污染转移和“去工业化”所实现的,而中国恰恰就是他们大规模转移产业时的一个重要的承接点。中国环境危机的加深也与这种全球尺度的产业转移有关,这迫使中国需要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就要直面环境危机。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还需要提高,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中国很难像西方国家一样,在通过全球化把污染最重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的同时还占据着价值链最高的位置。中国既没有去工业化的同时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的选项,也无法在道义层面支持大规模的国际污染转移。中国需要在被挤压的空间里,处理这些复杂的矛盾,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这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基本上没有先例可参考。
一种自上而下的、以顶层绿色理念来引领、统筹发展与环保的治理模式确实可以非常高效。我们在雾霾治理这个事情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中央政府设定量化的绩效考核目标,然后建立一整套的监测体系,使地方政府很难有“作弊”的空间,再通过像中央环保督察等各种各样纪律性的手段,迫使大家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手抓”。
但这套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非常强调供给侧的调整,比如通过行政手段要求钢铁厂减少产能,而不是通过激发消费侧的绿色需求,推动产业的主动转型升级。虽然短期内这种“供给侧环保主义”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走到一定的程度会遇到瓶颈,尤其是当这种调整的经济代价无法通过消费侧的新需求来进行消化的时候。如果消费者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没有被充分调动,不愿为更绿色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买单,那么就很难有不断涌现的创新来填补在供给侧被“消灭”的旧有产能,引领经济逐步转型升级。
对话地球:书中提到了许多在中国环保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曲格平、潘岳、梁从诫、于晓刚、汪永晨、解振华等。但近年来,似乎鲜少有类似的“环保斗士”或政治明星涌现。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马天杰:雾霾治理开始后,中国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绿色发展体系,极端的发展主义被摒弃。我在采访中听到这样的说法:以前当污染事件发生时,很多老百姓会联系当地的环保组织,请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抗争。后来,有了12345环保热线这样一个官方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加上中央环保督察,本来需要环保组织和媒体来曝光的事情,自然而然被纳入这个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了。所以民间力量在污染监督方面的作用变小了,也不太会出现过去那种全国性的、以揭露环境问题为主的的环保英雄形象。
三十年来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是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过去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需要培育民间力量去进行调查和监督,通过自下而上的博弈争取一个好一些的结果。随着环境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政府的管理能力变强了。比如在雾霾治理中开始应用的大气模型工具,可以告诉坐在北京的决策者,如果关闭河北的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污染源,或者控制它的污染水平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北京的PM2.5就能下降几个点。就好像在一个沙盘上,决策者可以去运筹帷幄,协调环保和发展。以前,可能真的需要环保志愿者在河边守着一个排污管, 发现问题就汇报给环保局。现在,随着卫星地图、污染源数据库、无人机、模型等技术手段被纳入到环境治理的体系,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对话地球:环保主义与发展主义之间的角力是本书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你看来,是否有案例表明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实现了较为理想的平衡?
马天杰:我觉得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环境和发展的协调统一, 虽然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雾霾治理到“双碳”, 中国找到了一个独特的配方,以环境目标作为一种激励和鞭策, 把经济和产业体系朝更具竞争力的这个方向去引领。绿色产业政策是过去十几年趟出来的一条很重要的路, 这条路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范式转变。
环境的约束, 比如PM2.5标准,或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这些在以前可能会被认为是镣铐, 是发展的负担, 是额外的成本。但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这些约束如果用得好、用得有策略的话, 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发展的动力。 通过给全国范围的经济提供绿色的约束, 可以制造一个良性的压力, 把那些高污染的、落后的生产能力淘汰掉, 给新的、绿色的、有竞争力的生产力腾出一个空间,然后让他们在这个绿色的约束的条件下, 不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最后甚至可以在国际上产生一种新的竞争力, 获得一个新的市场。
但这条路目前只走了一半。虽然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低碳制造业有潜力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但“绿水青山”距离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一直有回到旧有的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冲动,这样的张力恐怕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对话地球:书中提到,如果环保部能在项目规划前期就起决定性作用,那它本应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府部门之一。除了环评、生态红线这些政策工具,还有哪些工具或机制可以为极端发展主义提供约束?
马天杰:现阶段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部门层面的政策, 而是是所谓的“绿色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在宏观经济的层面去施加一个绿色的约束。虽然部门级别的工具, 比如说环评、节能评估,会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宏观的层面, 把对经济的整体绿色约束建立起来。这样的约束性指标, 需要跨部门的政策工具才能实现的。最近几年,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的金融工具,类似于这样宏观经济层面的工具, 在绿色转型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三十年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聚焦于国内污染治理,而如今,气候问题已经与全球治理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你认为中国在当前气候与环境治理中的机遇在哪里?
中国在协调发展和环保这条路上探索的经验值得很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借鉴。当下一个很好的机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当口,特别是像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国家,他们有发展的渴望,也有向中国学习这套模式的愿望。我认为现在是很好的机会把这套中国模式进行总结,尝试把其中一些经验教训,传达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伙伴。尤其是在美国放弃全球的环境领导力的时候,更应该做这件事。其实,城市之间的交流已经在发生,比如北京把雾霾治理的经验跟雅加达、德里交流。更大层面的这种环境治理模式的交流也是。这本书之所以用英文来写,也是希望对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感兴趣的这些国家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林孜,中国项目总监。她于2019年加入对话地球,曾经担任北京办公室运营总监。她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相关工作,参与并主导了多个气候变化、能源、农业、海洋等领域的传播项目。她拥有伦敦大学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